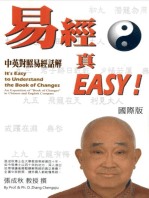Documentos de Académico
Documentos de Profesional
Documentos de Cultura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PDF
Cargado por
Thuận Trương AnhTítulo original
Derechos de autor
Formatos disponibles
Compartir este documento
Compartir o incrustar documentos
¿Le pareció útil este documento?
¿Este contenido es inapropiado?
Denunciar este documentoCopyright:
Formatos disponibles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PDF
Cargado por
Thuận Trương AnhCopyright:
Formatos disponibles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 ”的解读
许明龙
内容提要 礼仪之争传入欧洲后,引起法国知识菁英的广泛关注。 孟德斯鸠至迟自
1713 年起就关注礼仪之争,但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是冷眼旁观。 他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国的
绝大多数主要著作,还曾与来自中国的黄嘉略和自中国返回欧洲的傅圣泽进行长谈,从阅
读和谈话中汲取了大量的信息,作出了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他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
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 他对中
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
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关键词 十八世纪 法国 孟德斯鸠 礼仪之争 中国观
400 年前的 1610 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此前,他已指定龙华民接替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之职 ,
被后世称作“礼仪之争”的传教策略分歧由此开始孕育。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远非单纯的宗教事件 ,
而是掺杂着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间的国家利益之争,罗马天主教教廷与法国国王的权力之
争,以及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天主教修会或传教团体之间的宗派之争。
礼仪之争原本限于传教士内部,自入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明令禁止中国礼仪后,引发中国教
徒不满,遂扩展至普通教民。为寻求罗马教廷的支持,对立的双方把争论带到了遥远的欧洲 ,并且纷
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论点,从而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引发了一场了解、研究和诠释中国文化的大辩
论。这场争论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对中国的了解 ,使欧洲人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成为中西文化交流
史上绚丽多姿的一幕,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入华传教士所始料不及的 。
18 世纪的法国正处在革命前的启蒙时代 ,知识界热切希望借他山之石为病入膏肓的法国找到一
剂改革良方,教会人士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理所当然地引起他们的关注,并依据各自的了解和理解
作出不尽相同的解读。
本文试图着重探究的是被后人称作启蒙思想家的孟德斯鸠 。 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和
发生在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争。现有材料表明,他至迟在 1713 年就关注此事,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
他对争论双方的基本看法。他对礼仪之争的起因与过程的关注一点儿也不比当时关心此事的其他
人少。他在自己的笔记《地理》中写道: “从菲律宾来到福建福安县的两位多明我会士,在对中国人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29
的习俗所知甚少的情况下,便制定宗教活动的规矩。 男女一起聚集在教堂里,其中包括幼年时便受
命守贞的年轻姑娘。中国由此开始驱逐传教士。 妇女们为自己的贞操发誓,在教堂中集会,与神职
人员交往并参与圣事,还要面对面的单独忏悔,此外还有临终涂油和男子不得娶妾 ,等等。 当地官员
下令斥责这两位神甫和基督教信徒 。”①
孟德斯鸠不但关注着礼仪之争的发展 ,甚至还了解到一些细节。 例如,他在巴黎逗留期间,从他
的中国朋友黄嘉略那里听到了关于颜珰的故事: “科农主教颜珰在福建首府买了一所房子 ,准备改建
成教堂。为了与另一所非教徒住宅有所区别,他把大门扩大,使之大体上像我们这里的教堂大门那
样,并漆成红色( 红色被认为具有避火的功能) ,可是,红色是中国皇帝和庙宇专用的颜色 。不久就发
生了骚乱。居民们聚集起来大声叫嚷,说整条街道的福气都让这几扇门吞噬了 。 他们朝这所房子扔
垃圾,高声咒骂,闹得不可开交,改建工程不得不停下来。”②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位福建宗座代牧颜珰大人后来把事情闹大了 。 他于 1693 年颁布一道指令,
彻底否定耶稣会士所主张的关于中国礼仪的做法 ,并要求他辖区内的所有传教士和奉教者一体遵照
执行。他的做法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困难重重 ,遭到许多耶稣会士的反对,中国教民更是坚决抵制。
颜珰为争取教廷对他的支持,派人将他这份指令送往罗马。 颜珰的举措激化了礼仪之争,把原来局
限于入华传教士内部进行的争论带到了罗马教廷 。
小事如此,大事也如此。 对于罗马教廷先后两次派往中国的特使多罗 ( Tournon) 和嘉乐 ( Mez-
zabarba) 入华的活动,孟德斯鸠在笔记《随笔》中也留下了记述: “多罗抵达后,耶稣会士聚在一起,向
他介绍皇帝的情况,让他明白,他只要与皇帝交涉就可以了。 而实际上耶稣会士们与皇帝的看法始
终保持一致。多罗对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说: ‘你别管了,我会让你脱身的。’皇帝明白了他们之间的
分歧后说道: ‘看看这些人,他们在全中国劝说皈依基督教,指责我们的礼仪,其中一些人说是应该支
持他们的做法,另一些人说不行。于是激烈争吵起来。更有甚者,教宗也插上一手,试图替我的帝国
拿主意。’皇帝竭尽全力让多罗改变想法。皇帝起先盛情款待多罗,后来给他送去一些上谕,说他既
糊涂又无知。多罗回复皇帝说,他感谢皇帝陛下,吃点苦头也高兴。 再后来,多罗被送到澳门,把他
交到对他怀有敌意的葡萄牙人手中 。这些葡萄牙人说,多罗阻止那些不借道葡萄牙前来中国的传教
士进入澳门。
多罗发布了他的南京教谕,并通告说,教皇的圣谕即将送到澳门。 教皇的圣谕送达时附有一道
谕旨,要求每一个传教士必须遵守谕旨的规定 。 北京的一位方济各会负责人要求大家发誓执行教
谕,结果被抓,带上了九条镣铐。
后来又来了嘉乐,他什么也没做成。 他说他来华的使命仅仅是向皇帝致敬。 皇帝遂施加压力,
让他撤销圣谕。他泪流满面地说,他是他的主子派来的,无权撤销主子的圣谕。 两个月后,嘉乐启程
返回,行前表示,他将劝说他的主子撤销圣谕。”③
很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礼仪之争中发生的事情,孟德斯鸠有相当多的了解。 正是依据这
些了解,他才得以对这场争论作出自己的判断 ,而不是如同有些人所说,他只是因为听信了傅圣泽的
① 《孟德斯鸠全集》( Oe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第 16 卷,牛津 2007 年版,第 391 页。
②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第 114—115 页。
③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 Louis Desgraves, Pensées et le Spicilège) ,
Montesquieu, 巴黎 1991 年版,
第 809 页。
30 世 界 历 史 2011 年第 4 期
胡言乱语,才对礼仪之争中的耶稣会士采取极不友好的态度。 不但如此,他还透过礼仪之争的种种
具体内容,诸如中国人究竟是无神论者、自然神论者抑或唯理主义者,敬孔祭祖是否迷信活动,是否
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等等,从这些争论中他看到了隐藏在礼仪之争背后的天主教会内部派别之间的宿
怨。他在笔记《随 想 录 》中 写 下 的 话 可 资 证 明: 耶 稣 会 士 和 冉 森 派 教 士 把 他 们 的 争 吵 带 到 中 国
去了。①
派别之争所暴露的充其量只是教会内部的不和与矛盾 ,孟德斯鸠透过派别之争还看到了来自不
同国家的传教士所代表的国家利害的冲突 ,在这一点上,他比就事论事地讨论礼仪之争中谁是谁非
的人高出了一头。请看他在《随笔》中写下的话: “无论是葡萄牙人、德国人或法国人,耶稣会士们都
相互视为仇敌,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则把所有耶稣会士统统视为仇敌,因而他们的名声很坏。 有一
天,傅圣泽在一个大堂上恭候皇上时 ,听到一个中国人说: ‘你看这些家伙,比和尚还坏。’傅圣泽神甫
还说,法国耶稣会士把梅 纳 公 爵 送 来 的 两 架 仪 器 呈 给 皇 上 时 ,德 国 耶 稣 会 士 出 于 嫉 妒 而 把 机 器
弄坏。”②
细节虽然来自傅圣泽的叙述,但孟德斯鸠显然从中看到了入华传教士们为各自的国家利益而相
互拆台的事实。当时关注礼仪之争的法国知识界 ,大多是从广义的文化层面来观察这场旷日持久的
争论的,孟德斯鸠虽然也不例外,但透过表象他还看到了隐藏在这场争论后面的利益之争 ,却不能不
说是他的过人之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贪婪地阅读有关礼仪之争的各种文献,一方面以局
外人的目光对这场争论作壁上观 ,而不像有些人那样明确地支持一方 ,反对另一方。
从总体上看,孟德斯鸠看待礼仪之争的冷峻态度 ,一则源自上述他对礼仪之争实质的分析 ,一则
源自他的宗教观念。他认为,宗教是用来指导人的心灵的,是为人正直诚实的最佳保证; 宗教的规矩
不是为了好,而是为了最佳,不是为了善,而是为了至善。 他还认为,宗教包含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
普遍精神之中,而普遍精神则是地理、气候、风尚、习俗、法律、宗教共同影响下产生的结果。 各个国
家情况不同,普遍精神也就不同。倘若不考虑普遍精神中的其他因素,单单想要改变一个国家人民
的宗教信仰,那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与其强行改变一种宗教信仰,莫如尊重人们原有的宗教信仰。 他
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 “勃固人所信奉的宗教的主要教义是 : 不杀、不偷、不做下流无耻的事、不做
任何让众人不快的事,反之,要竭尽全力为众人做一切好事。 他们相信,能做到这些的人,不论信奉
什么宗教,都能得到拯救。正因为如此,勃固人民尽管既贫且傲,却都以慈爱和同情之心对待不幸
的人。”③
能做好事的人,不论信奉什么宗教,都能得到拯救。 这也许就是孟德斯鸠的基本宗教观念。 既
然如此,又何必非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他人呢? 所以,孟德斯鸠对于基督教在南美的传教活动
中借助暴力强迫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的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认为那是一种卑劣的殖民活动。 尽管由
于中国拥有数千年文明,人民富有教养,统治者治理有方,传教士因而没有沿用对付南美洲土著居民
的那种野蛮手段在中国传教,但孟德斯鸠依然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不可能开花结果的 。
事实表明,发生在中国的所谓礼仪之争,同样是由某些传教士不顾当地的风尚与习俗 ,强制推行欧洲
①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201 页。
②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805 页。
③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475 页。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31
天主教的那套宗教礼仪,进而引起民众和官方的反感和抵制而引起的。 出于这种认识,他对礼仪之
争的基本立场就不言而喻了,那就是不支持基督教的入华传教活动 ,不支持礼仪之争中的任何一方。
所以,我们看到,孟德斯鸠既不为耶稣会士说好话 ,也不为与耶稣会士对立的一方辩护 。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他不重视这个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极佳机会 ,恰恰相反,正如前面所说,他全
神贯注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倾听着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进而形成了他对这场轰动法国乃至欧洲的
重大事件的总体看法: “但是,一种从遥远国家传入的宗教,一种与当地的气候、法律、习俗和风尚全
然不能适应的宗教,并不会因其神圣而大获成功,这种情况尤以专制大帝国为最。 起初,外国人受到
容忍,因为那些东西似乎并不损害君主的权威 ,因而没有引起注意,当地人处在极端无知之中。 一个
欧洲人可以利用他所获得的某些知识博得赏识 。 起初这样做是有效的,可是,这是一个因其性质而
特别需要太平的国家,稍有风吹草动,政权就可能被推翻,所以,当外来者取得了一些成就,发生了某
些争执,利益相关的人就引起了警觉,新近传入的宗教和传播这种宗教的人于是就被禁止 ; 更因为传
教士之间爆发了争执,当地人遂开始憎恶这种新的宗教 ,就连前来传播这种宗教的人,彼此也不能达
成一致意见。”①
上面这段论述尽管只字未提中国,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段话实际上是对明末清初百余年间
天主教入华活动的一个扼要而又精辟的总结 ,我们不能不佩服孟德斯鸠的高度概括能力 。
在这段话中,他首先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难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气
候、法律和风尚等等全然不能适应。为什么传教事业起初似乎颇有进展呢 ? 他认为有三个原因。 其
一,中国人对基督教究竟为何物处于无知之中 ; 其二,传教士没有损害君主的利益,相反,他们从西方
带来的某些科学知识和绘画、修理机械等技艺还博得了皇帝和宫廷的欢心 ; 其三,以儒家为代表的中
国传统思想对外来的宗教并不抵触 。关于儒教对外来宗教的态度,孟德斯鸠是这样说的: “所有传入
中国的宗教都不被看作新的宗教,而仅仅是对原有宗教的一种补充 ,孔子既然听凭崇拜鬼神,因而也
就为这些外来起补充作用的宗教敞开了大门 。”②
于是,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最初的困难之后 ,渐渐有了起色,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似乎获
得了长足的进展。孟德斯鸠这样描述这种状况: “在这个王国里,起初大家对传教士采取容忍态度,
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让他们立足并非什么大事情。”③后来为什么又失败了呢? 事情发生
变化的责任完全在于传教士自己: “但是后来他们试图拥有一切,改变一切; 他们不懂得,在任何活动
中一定不能过于张扬,即便是传播福音。”结果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可悲的: “于是,他们在站稳脚跟之
前就被赶走了。”④
当然,孟德斯鸠并非那样天真,以为传教士们当初如果能够收敛一些 ,他们在中国的事业就可能
取得成功。在他看来,西方基督教传播在中国的失败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之所以不可能皈
依,是因为那里的政府和宗教完全是同一回事 ,两者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那就是同一的伦理道德,
所以,必须首先推翻政府,然后才能改变宗教信仰。”⑤
①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下卷,第 501 页。
②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498 页。
③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第 391 页。
④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第 391 页。
⑤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第 392 页。
32 世 界 历 史 2011 年第 4 期
他在这里表述的意思是,中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不存在能够与世俗统治者抗衡的宗教势力 ,
外来的基督教想要在中国站稳脚跟 ,首先必须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这既不是罗马教廷的目的,也
不是传教士的初衷,更不是他们能够办成的事情。
此外,
孟德斯鸠也深知,
无论教会人士和学者对中国人的宗教和信仰如何定位———无神论、自然神
论、 偶像崇拜和迷信……最重要的事实是,
唯理论、 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信仰、
习俗和
礼仪,
而构成普遍精神的这些因素无一不是根深蒂固乃至牢不可破的。要中国人接受基督教,首先必
须让他们放弃所有这一切,
而这岂是传教士们所能做到的。所以他说: “我不希望有人去教化中国人,
因为,
必须先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宗教是虚假的,
他们是劣民,
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基督教徒。
”①
退一万步说,基督教的传教事业纵然在中国获得了部分成功,其后果可能也会是灾难性的,因
为,“如果国王皈依了,他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如果人民皈依了,他们就成了国王的敌人。”所以,孟德
斯鸠的结论就是: 所有向这些国家派遣的传教团,都是坏事! ②
很显然,孟德斯鸠不仅对礼仪之争的来龙去脉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对十七八世纪基督教的入华
传教活动总体把握比较准确。就此而言,在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中,能与孟德斯鸠比肩的恐怕只有伏
尔泰。伏尔泰把他的《路易十四时代》第 39 章辟为议论礼仪之争的专章,题为“关于中国礼仪之争,
这些争论怎样促使中国取缔基督教 ”。在叙事的详尽方面,伏尔泰远在孟德斯鸠以上,对于这次传教
活动以失败告终的表面原因,他与孟德斯鸠的看法不谋而合: “前来帝国传教布道的外国人之间的分
裂不和,使他们传布的宗教名誉扫地。 满清朝廷对欧洲人注意了解之后,得知不仅传教士内部四分
五裂,而且在广州登岸的外国商人也分成派别 ,彼此不共戴天。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更加被人
贬低。”③
然而,对于礼仪之争和传教失败的深层原因的分析和认识,伏尔泰似乎不如孟德斯鸠。 他虽然
也在《哲学词典》的“论中国”条目中责备耶稣会士过于狂妄,心目中只有基督教和教皇,以至于令中
国人厌恶,最终遭中国人人唾弃。但是,他却没有向前再进一步,没能像孟德斯鸠那样,从总体上回
答这样一个问题: 产生于一种异质文化的宗教,如何才能在拥有不同文明的国度里立足生根 。
孟德斯鸠对于礼仪之争和传教活动的总体看法 ,决定了他无意评判参与争论的双方谁是谁非。
在他看来,无论是否曾经有过礼仪之争,无论哪一方在争论中占了上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都肯定
不会成功,这场争论是无谓的争论,而传教的失败则是必然的失败。 在这一点上,伏尔泰似乎也比不
上孟德斯鸠,在《路易十四时代》的第 39 章中,他明确地支持李明,斥责颜珰,甚至偏袒耶稣会士,否
认他们在澳门虐待教皇特使多罗 。
在如火如荼的礼仪之争中,了解中国成了每一个关注和参与这场争论的法国知识界的迫切需
求,实地考察当然是最佳途径,弗雷莱和伏尔泰都曾经有过前往中国的念头 ,但都未能如愿成行。 所
①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531 页。
②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396 页。
③ 伏尔泰: 《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600 页。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33
以,阅读便成为了解中国的最主要途径 。从礼仪之争在中国初露端倪的 17 世纪上半叶,到这场争论
逐渐平息的 18 世纪中叶,参与争论的双方为阐述己方的立场和观点 ,为驳斥对方的立场和观点,不
断撰写并出版了难以数计的文章、小册子和书籍。 这些著述就是法国知识界了解这场争论的主要
途径。
众所周知,在礼仪之争中持截然相反观点的双方 ,一方是大多数入华耶稣会士,另一方是包括外
方传教会士、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在内的入华传教士 。入华耶稣会士人数较多,汉语水平较高,
大多能阅读中国的古代经典,而且以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艺博得了中国皇帝的欢心 ,得以进入皇宫,
接触上层高官和文士,对古老的中国文化有较多的了解 。他们撰写了不少信函和报告之类的文字数
据传回法国,获得广泛的好评。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解读和介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主宰着法国
的舆论。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代表的另一方则不同 ,他们坚决反对利玛窦在传教活动中所倡导并执
行的适应政策,对天主教教义和教规秉持执拗和僵化态度 。由于他们不像耶稣会士那样喜欢在上层
活动,而是深入穷乡僻壤,接触普通百姓,所以对中国人的迷信落后等习俗有较多的直观了解 ,出现
在他们的中国报导中的中国形象自然与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形象相去甚远 。
凭借阅读这些出自不同观察者笔下的著作 ,孟德斯鸠等人获得了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并依据
各自的理解和分析作出对中国的判断,发表文章和专著。 当今研究 18 世纪中国在法国的形象的学
者,习惯于将当时就中国表示意见的法国知识界区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 ,其一是颂华派,其二是贬华
派,前者的首领是伏尔泰,后者的领头人是孟德斯鸠。
顾名思义,贬华派就是说中国坏话的人。 孟德斯鸠之所以被视为贬华派的领头人,主要就是因
为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有许多批评或斥责。事实确实如此,自从《论法的精神 》问世之后,此
前几乎得到一致承认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开始蒙上了阴影 ,法国知识界在中国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两种
不同的看法,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夜,美好的中国形象彻底为丑陋的中国形象所取代 。
一些学者认为,孟德斯鸠在中国问题上的偏执首先应该归咎于傅圣泽,是傅圣泽的一席话改变
了孟德斯鸠对待中国的态度,从此对耶稣会士采取一律不予信任的态度,转而千方百计寻找与耶稣
会士相反的报导和论述。法国已故汉学泰斗艾田蒲便是持这种看法的著名学者之一 ,他在他的名著
《中国之欧洲》中,一再严厉斥责傅圣泽向孟德斯鸠灌输了中国的负面形象 ,从而严重影响了孟德斯
鸠的中国观。“如同当时大多数学人和好奇的人们一样 ,孟德斯鸠从《中华帝国全志 》中索取他所需
的大部分信息。我们可以设想……早在 1729 年,傅圣泽就摧毁了孟德斯鸠对杜赫德的敬重 。”①
“我只想指出,孟德斯鸠在遇到前耶稣会士傅圣泽之前,对中国的评价是好的,傅圣泽对他进行
说服,劝他对于耶稣会士的那些报导不要给予丝毫的信任 。”②
正如艾田蒲所说,孟德斯鸠于 1729 年 2 月在罗马会见了傅圣泽,与这位曾在中国居留 22 年的
耶稣会士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谈话。作为一个入华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 ,在有关中国的历史和宗教等
问题上,他与大多数入华耶稣会士持不同看法,也不像他的同僚那样赞美中国。 孟德斯鸠事后就这
几次谈话做了笔记,文字较长,我们只能从中引述不多的几段: “国家一旦积弱,治理无方,就会经常
受盗贼侵扰。由于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妇女生育力极强,倘若发生饥荒,粮食匮乏,村子里的领头人
① 艾田蒲: 《中国之欧洲》( Etiemble,L'Europe chinoise) 第 2 卷,巴黎 1898 年版,第 53 页。
② 艾田蒲: 《中国之欧洲》第 2 卷,第 65 页。
34 世 界 历 史 2011 年第 4 期
就会对村民说: ‘父老乡亲们,官府治理不好,我们快要饿死了,大家一起去找吃的吧! ’10 个人,
20 个
30 个人,就这样聚集起来。其他村子也是这样,随后两伙人相互争斗。胜者成为首领,败者归顺,
人、
队伍日益壮大,四处劫掠烧杀。其结果往往就是改朝换代。”
“皇宫像是一个蜘蛛网,皇帝就像是蜘蛛网中间的蜘蛛。 他一动弹,整个蜘蛛网就跟着动弹,别
人若是动弹,皇帝也不可能不动弹。”
“大凡皇帝权威所及,他不会把一个人的生命看得比一只苍蝇的生命更重。 不过,除此之外,他
倒是喜欢拥有宽厚仁慈的名声,他颁发一些上谕,强调人的生命和鲜血是如何珍贵。 中国的皇帝都
希望老百姓相信先贤的这个信条: 国家是一个大家庭,皇帝就是父亲。 所以,这位皇帝每年都要蠲免
某个省份的应纳之捐税。”①
傅圣泽的这些话确实给孟德斯鸠以深刻的印象 ,他把这些话稍加修改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全部
写进了他的传世名著《论法的精神 》,作为他认定中国的政体是专制主义的依据之一 。 在中国人听
来,傅圣泽的话确实有点尖刻,然而,我们却无法指责他是毫无根据地胡说八道 ,恶意诋毁,而只能说
他揭露了中国的阴暗面。然而,细心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就在这段谈话中,傅圣泽也没有忘记就中
国的皇帝说了几句好话。在另一处,傅圣泽还向孟德斯鸠谈及雍正对待西洋传教士的态度: “先帝驾
崩时,中国约有 30 万基督教徒。当今的皇帝不是应该继承皇位的那个皇子,他是基督徒的敌人,不
过,表面上他对他们还算公正。一位传教士在先帝的寝宫里说了一些有利于当今皇帝的一位兄弟而
有损于他的话,这是当今的皇帝把基督教徒视若敌人的原因。 这位皇帝下谕给一位总督,让他指控
基督教徒,用什么借口都可以。他宣称,基督教对中国构成危害,所以他只允许对帝国有用的欧洲人
留在中国,其余则统统遣送到澳门,不过,要善待他们,何况他们曾经为帝国做过好事。 多位传教士
要求留下,理由是他们需要祭奠长眠在中国的那些同伴。 有几位果然留在广州,其中有几位后来又
去往中国各地。”②
孟德斯鸠不是一个随风倒的人,对于别人的看法和意见他始终有自己的判断 。 他确实听信了傅
圣泽对中国的许多评论,但并非不加区别地一概吸纳。魏若望在他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 》中提
及,傅圣泽在罗马与孟德斯鸠会见时 ,曾赠送给他一本前不久出版的中国历史年表 ,魏若望接着说了
这样一句值得我们注意的话: “但孟德斯鸠并不愿接受傅圣泽的观点 ,因为他早与黄嘉略讨论过中国
编年史的问题,黄嘉略提到中国人确信他们的历史是从尧时代开始的 。”③
艾田蒲把孟德斯鸠中国观的形成归因于傅圣泽 ,魏若望已经指出,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 笔
者认为,此外还有一个能够有力地支持魏若望的论据 ,那就是时间不对。 众所周知,杜赫德的《中华
帝国全志》出版于 1735 年,专家的研究表明,孟德斯鸠阅读此书并做摘录和笔记的时间不会晚于
1739 年。④ 前面提到,孟德斯鸠是在 1729 年会见傅圣泽的,那么,傅圣泽如何能在《中华帝国全志 》
尚未出版之时“摧毁孟德斯鸠对杜赫德的敬重”呢?
其实,孟德斯鸠的中国观早在 1713 年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那一年他在巴黎认识了中国青年黄嘉
①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806、807 页。
②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805 页。
③ 魏若望: 《傅圣泽传》( John W. 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 - Franois Foucquet,
S. J. 1665 -
1741) ,
罗马 1982 年版,第 313 页。
④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 第 133 页。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35
略,并与之多次长谈。他与黄嘉略进行多次长谈后,留下了一份事后的追记《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
于中国的若干评述》。在这份文献中,孟德斯鸠已经明显地表露出他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如果中国
政府果真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优秀 ,鞑靼人怎能只用一天时间就成了它的主人呢 ? 历史上几乎没有
这种快速征服的先例。没有一个地方对入侵者进行过抵抗 ,入侵者如入无人之境,从未遇到抵抗。”①
这种看法显然有别于当时耶稣会士所传播的对中国的赞美 ,而与他后来执拗地认定中国的政体
是专制主义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孟德斯鸠早在会见傅圣泽二十余年之前,就已经对耶稣会士笔下
的中国形象提出质疑了。所以说,在孟德斯鸠的中国观形成时间上,还是魏若望说得对: “当孟德斯
鸠 1729 年 2 月 1 日会见傅圣泽时,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是专制主义的思想 ……”②
魏若望的判断是正确的,孟德斯鸠的中国观在他 1729 年会见傅圣泽时已经初步形成。 我们不
妨尝试着追寻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
1713 年他与黄嘉略在巴黎的会见和长谈
中首次显露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那时他是一个 24 岁的小青年。 黄嘉略所讲述的中国与耶稣会士
笔下的中国相去甚远,《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 》中甚至出现过“我相信,中国人
越被人认识就越糟糕。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之一 ”这类极度贬斥中国的话语。 尽管我们现
在无法确切辨明此类贬斥中国的言论究竟出自黄嘉略之口 ( 孟德斯鸠只是如实记录而已) ,抑或并非
黄嘉略所说,而是孟德斯鸠的发挥,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孟德斯鸠对这些话并不反感。
在礼仪之争大潮的推动下,孟德斯鸠此后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这种阅读不是泛泛的浏
览,而是精心的钻研,他边读边作笔记,记下摘录和概要,写下感想或评述。 仅在他的阅读笔记《地
理》中,就有包括《中华帝国全志》和《耶稣会士书信集 》等有关中国的重要著作近十种。 现存的《地
理》仅是这部笔记的第二册,第一册已经无从查找。不难想见,在已经丢失的《地理 》第一册中,很可
能还有不少与中国有关书籍的阅读笔记。1999 年出版的《拉布莱德孟德斯鸠藏书目录 》表明,除了
记录在《地理》中的那些图书外,孟德斯鸠在家乡拉布莱德还收藏有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基歇
尔的《图说中国》、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 》、尼厄霍夫的《出使中国记 》、西鲁
哀特的《中国政制和道德概述》等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 这些书籍总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装饰吧。 此
外,文献表明,他还阅读过刘应的《鞑靼史 》、德拉克鲁瓦的《成吉思汗史 》、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
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能够读到的重要的乃至次要的有关中国的著作 ,他都读过。 笔者过去
曾认为,孟德斯鸠偏爱商人和旅行家的游记,现在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 事实是,
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排斥耶稣会士的著作 ,正如《地理 》所表明,他不但读了,而且读得相当仔细认真。
艾田蒲也是这样说的: “如同当时大多数学者和好奇者一样,孟德斯鸠从《中华帝国全志 》中获得了
他所需的大部分信息。”③
但是,他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解读这些著作中的信息的 ,所以,这些信息不但向他展示了中国
的美好,也为他斥责中国的专制主义提供了依据 。
有人说,孟德斯鸠对耶稣会士抱有极深的成见,对他们有关中国的记述一概不予置信,反之,他
偏信商人和旅行家有关中国的游记 ,而在这些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往往是被扭曲或丑化的 。 支持这种
①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第 133 页。
② 魏若望: 《傅圣泽传》,第 312 页。
③ 艾田蒲: 《中国之欧洲》第 2 卷,第 53 页。
36 世 界 历 史 2011 年第 4 期
看法最有力的证据大概是《论法的精神》在 1757 年再版时,孟德斯鸠在第八章第二十一节中插入了
这样一句话: “我还可以请安逊勋爵这位伟人作证 ”①。
安逊( George Anson) 是一位英国水师军官,曾率领舰队作环球航行,因修理船舰和补充给养之
需,曾在澳门和广州作短暂停留,其间与中国官员和商人有过一些不愉快的接触。1748 年他在伦敦
出版了《1740—1744 年环球航行》(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 - 1744 ) 一书。书中记
述了英国人在与中国官员和商人打交道时所见到的种种丑恶现象 ,诸如官员办事效率低下,索贿却
十分积极; 商人贪婪狡猾不讲信誉; 百姓好逸恶劳,欺软怕硬等等。
孟德斯鸠完全相信安逊对中国人的贬斥 ,此事确实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相对于耶稣会士笔下的
同类文字,孟德斯鸠更重视非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报导 。笔者以为,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在当时
的法国,人们对中国的“颂”和“贬 ”极不平衡,主宰舆论的是耶稣会士的报导,对中国的负面报导比
较罕见,孟德斯鸠希望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所以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负面报导格外重视。 其二是孟
德斯鸠对耶稣会士存有戒心,怀疑他们的报导的真实性。 他在阅读《中华帝国全志 》时曾写道: “描
述中国的耶稣会士激情满腔。杜赫德提及的那八个省份中,我所见到的都令人钦羡,一切都美,一切
都好,一切都无与伦比; 大自然难道总是如此美好而不掺杂任何丑陋吗 ?”②
这种怀疑有时甚至到了根本不予信任的程度 。依然是在阅读《耶稣会士书信集》的笔记中,他写
道: “这些信件中到处都是千奇百怪的事实 ,当隐瞒真情对他们没有益处时,他们如实报导,而为了取
得人们的信任,他们就想撒谎。”③
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不错,孟德斯鸠确实说过不少讨厌耶稣会士的的话: “耶
稣会士,我怕他们。这群人围着我,到处都能找到我。 我若是冒犯了一位大老爷,我就躲开,再也不
见他。可是,耶稣会士却像宗教裁判所的那些家伙 。”④
不过,平心而论,他在这里不是对耶稣会士的总体评价 ,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的牢骚。 他的著作
出版后,耶稣会士总想从他的著作中挑刺找茬,指责他违背教义,对上帝不恭等等,致使他不得不忙
于应对,常常被弄得不胜其烦。
当然,孟德斯鸠也曾严厉指责耶稣会士 ,这次不是指责某一位或某几位耶稣会士 ,而是针对耶稣
会士在礼仪之争中的的总体表现 。他在评论《耶稣会士书信集 》第十九辑报导的雍正皇帝对礼仪之
争的看法时写道: “我们看到,中国人相信,所有人民都崇敬天或天主,区别仅在于各国的礼仪不同,
比如,满人与汉人的礼仪就不相同。 皇帝说,我并没有禁止乌尔陈敬天,但他是满人,那就应该按照
满人的礼仪敬天。由此可见,耶稣会士既欺骗了中国人,也欺骗了欧洲人,他们让基督教徒以为他们
的信仰就是中国人的信仰,让中国人以为基督教徒的信仰就是中国人的信仰 。”⑤
孟德斯鸠在这里对耶稣会士的批评绝对没有错 ,耶稣会士没有理由感到冤枉,我们也没有理由
指责孟德斯鸠无端丑化乃至敌视耶稣会士 。他们为了顺利推进入华传教事业,不是竭力试图让中国
人相信,基督教其实并非外来宗教,其教义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并无根本冲突吗? 他们不是力图让中
①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卷,第 133 页。
②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第 157 页。
③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第 369 页。
④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396 页。
⑤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第 369 页。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37
国人相信,上古时代的中国人所信奉的就是与基督教相似的宗教 ,只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广泛传播,
中国人把自己古老的信仰渐渐忘却了而已吗 ? 耶稣会士中的傅圣泽、白晋等索隐派还挖空心思地到
中国的古籍中去发掘所谓的证据 ,这难道不是既骗了中国人,也骗了欧洲人吗?
其实,孟德斯鸠绝非一概讨厌耶稣会士,不但如此,有的耶稣会士还是他交往数十年的挚友,卡
斯泰尔神甫( Louis - Bertrand Castel) 就是其中之一。1733 年,《罗马盛衰原因论 》脱稿后,孟德斯鸠
诚心诚意地请卡斯泰尔神甫审读; 并且把在巴黎求学的儿子委托卡斯泰尔代为照管 。 孟德斯鸠弥留
之际,为他做临终忏悔的有两位神职人员,一位就是卡斯泰尔神甫,另一位也是耶稣会士: 爱尔兰人
鲁斯( Bernard Routh) 。不但如此,他对耶稣会士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很是赞赏,否则他不会执意把自
己的儿子送进耶稣会士主持的路易大王学校 。① 他也知道,耶稣会士的素养和才干高于在礼仪之争
中与之对抗的多明我会士: “请把一个耶稣会士和一个多明我会士派到一个新发现的国家去 ,一年之
后你就会获悉,那个耶稣会士被请进了王宫,而那位多明我会士则混迹在流氓恶棍之中 。”②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对待耶稣会士的态度并非秉持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的。笼统地指责他敌视耶稣会士,偏听偏信站在耶稣会士对立面的传教士和商人 、旅行者一方,既不
公正,也不是事实。
关于中国的负面报导他并非一概采信 ,对于那些明显的不实之词,不管来自何方,他都认真地予
以剔除。比如,在他阅读雷诺多 ( Renaudot) 翻译的《两位穆斯林旅行家的印度和中国游记 》的笔记
中,为他代笔的秘书记下了这样的话: “有人说中国人是野蛮民族,他们食用人肉。”孟德斯鸠审读时
断然划掉了 这 句 话,并 就 此 亲 笔 写 道: “虽 然 这 是 两 位 阿 拉 伯 旅 行 家 的 记 述,但 我 认 为 此 事 不
可信。”③
那么,如何解释孟德斯鸠对耶稣会士的怀疑和不信任呢 ? 他在处理耶稣会士及其对立面关于中
国的报导时,秉持什么价值判断标准呢? 我以为,这与他早早就认定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有着
密切的关系。
虽然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 ,断言从这一天起,孟德斯鸠就把中国视为专制主义国家 ,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与黄嘉略谈话之前,已经开始怀疑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形象了。 在他的心目
中,黄嘉略的可信度比耶稣会士不知高出多少倍 ,因为他是中国人。 我们知道,黄嘉略自七岁起就由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两位神甫抚养 ,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他在礼仪之争所涉及的种种问
题上,所持观点必然与耶稣会士大相径庭。 孟德斯鸠与黄嘉略谈话之后,带着他已经初步形成的想
法,孜孜不倦地阅读了上面提到的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 ,而他在这些著作中所汲取的养料,进一步加
深了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的看法 。 所以说,他与傅圣泽 1729 年在罗马的会见和交谈只是强化
了他业已形成的中国观而已,并不是促使他从颂扬中国变为批判中国的原因 。
孟德斯鸠把中国视为专制主义国家,主要是他的政体理论体系使然,而绝非单单基于他所获得
的信息。他在《论法的精神·序》中明白无误地说过: “我提出了一些原则,于是我看到: 一个个各不
相同的实例乖乖地自动对号入座 ……”④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这是他根据自己确定的原则作
①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156、 429 页。
157、
② 路易·戴格拉夫: 《孟德斯鸠的随想录和随笔》,第 304 页。
③ 《孟德斯鸠全集》第 16 卷,第 87 页。
④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卷,第 2 页。
38 世 界 历 史 2011 年第 4 期
出的一个判断; 从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中获得的具体材料 ,则是一个个“对号入座”的实例,尽管不一
定是“乖乖”,也不一定是“自动”。 换言之,他认定中国是专制主义国家之后,一切有关中国的信息
都被他用来为这一论断服务。反过来,他所获得的许多( 并非所有) 信息也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这一判
断正确无误。笔者以为,孟德斯鸠的“原则”和“实例”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这个无始无终的循
环: 鸡生蛋,蛋生鸡。
孟德斯鸠凭什么一口咬定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主义国家 ? 他当然有一套相当完备
的理论,这个判断是他从气候、人口、地理环境、宗教、经济、政治,以及他所强调的“普遍精神”引申出
来的。至于他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当初在法国就有截然
相反的两种意见。如今即令在中国,也依然是见仁见智。 近年来,有几位学者就此撰写了长文展开
讨论,台湾学者龚鹏程对孟德斯鸠的这一见解痛加驳斥 ; ① 大陆学者侯旭东认为,这一“结论包含着
相当多的想象与幻想的成分”②。前不久,大陆的另一位学者黄敏兰则撰文反驳侯旭东,认为“孟德
斯鸠评论中国并非出于偏见”③。看来,这个问题还得争论下去。但是,本文仅限于探讨孟德斯鸠对
礼仪之争的解读,厘清礼仪之争为他提供了哪些启示,分析他对礼仪之争中的双方各持什么态度。
至于他的“中国是专制主义国家”的论断能否成立,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研讨的范围,有机会时将另
文探讨。
[本文作者许明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6]
( 责任编辑: 任灵兰)
① 龚鹏程: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
③ 黄敏兰: 《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which showed extraordinary creativity,impacted the whole human
society and demonstrated inherent limitations.
Xü Minglong,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by Montesquieu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once introduced to Europe,drew widespread attention
among French intellectual elite. Montesquieu started watching the controversy since 1713.
But,instead of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controversy,he sat on the sideline. He read most of
the major works related to China that were available at that time in Europe. He also conducted
long conversations in Paris with Mr. Arcade Huang,a gentleman from China,and in Rome
with Father Franois Foucquet,a missionary returned from China. All of hi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and his general concept of China were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he accumulated from reading and conversations. To him,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was nothing but nonsense,and the evangelization in China was doomed to failure.
From his own perception of China,his observation of China is a blend of praise and censure.
He pointed out both good and bad aspects of China and finally defined Chinese government as
despotic.
Li Yongsheng,A Study of German-American-Chinese Entente of 1907 - 1908
In 1907,the German Government raised the proposal of German-American-Chinese
Entente to cope with the agreements about China among Great Britain,France,Japan and
Russia. There is currently a prevailing viewpoint holding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appointed
Tang Shaoyi as special envoy to thank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or remitting the indemnity of
1901 nominally while Tang's actual task was to establish the German-American-Chinese
Entente. In fact,the Qing Government showed little enthusiasm toward the proposal of Entente
initiat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and the secret talk betwe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and
Tang Shaoyi ended the proposal of Entent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t first told the German
Government that it would like to take the Entente issue. But soo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changed its tune,signed the Root-Takahira Exchange of Notes and declined Germany's
proposal. The German-American-Chinese Entente Proposal was hazardous to the United State
and China,so it was declined by them.
Meng Zhongjie,On the Change of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Weimar Germany: The
Case of the Eight-hour Working Day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Weimar Germany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cooperation to opposi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ight-hour working day was the exampl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eimar Germany,the eight-hour working day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the revolution and demobilization,so that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También podría gustarte
- It'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Book of Changes (English and Chinese): 易經真EASY(中英雙語版)De EverandIt'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Book of Changes (English and Chinese): 易經真EASY(中英雙語版)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礼仪之争"研究综述 PDFDocumento4 páginas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礼仪之争"研究综述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护教篇 德尔图良著 涂世华译Documento210 páginas护教篇 德尔图良著 涂世华译riverli.china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巨人的一代(上)Documento283 páginas巨人的一代(上)Mantis100% (1)
- 02 《中国基督教会史》第一部 福音初临 - 唐朝景教Documento3 páginas02 《中国基督教会史》第一部 福音初临 - 唐朝景教453628390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陈焕强 明清官绅反基督宗教的道教文化资源探析Documento6 páginas陈焕强 明清官绅反基督宗教的道教文化资源探析YING Huanqiang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從天儒合一到東西分歧 歐洲中國觀的演變Documento18 páginas從天儒合一到東西分歧 歐洲中國觀的演變ninoouo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一体两面 基督教本地化论略Documento14 páginas一体两面 基督教本地化论略zhang nu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一体两面 基督教本地化论略Documento14 páginas一体两面 基督教本地化论略zhang nu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论宋元时期的外来宗教Documento13 páginas论宋元时期的外来宗教api-3699895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第六期通訊Documento16 páginas第六期通訊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CH03Documento40 páginasCH03jeepjeep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初探 张先清Documento17 páginas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初探 张先清FedericoEliaFrancescoValenti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 中国政教关系再论 (1) -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Documento1 página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 中国政教关系再论 (1) -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milkpartner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坎特伯雷故事》的朝圣旅程与基督教传统 肖明翰Documento6 páginas《坎特伯雷故事》的朝圣旅程与基督教传统 肖明翰zhi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易經:6.1 王宏超:〈宗教、政治與文化:索隱派與來華傳教士的易學研究〉,頁37-44Documento8 páginas易經:6.1 王宏超:〈宗教、政治與文化:索隱派與來華傳教士的易學研究〉,頁37-44Joey ʕ •̀ o •́ ʔ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盛世下的忧患 中西关系视角下的康雍乾盛世 欧阳哲生Documento13 páginas盛世下的忧患 中西关系视角下的康雍乾盛世 欧阳哲生yw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Documento7 páginas"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s loo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17世纪西班牙在华方济各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 叶君洋Documento9 páginas17世纪西班牙在华方济各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 叶君洋yw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协同书》Documento356 páginas《协同书》Leon Leo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单士厘的犹太观 张礼刚Documento2 páginas单士厘的犹太观 张礼刚jing GE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早期耶稣会士与《道德经》翻译Documento35 páginas早期耶稣会士与《道德经》翻译sandyjiang100% (1)
- 04 《中国基督教会史》第三部 福音三临Documento17 páginas04 《中国基督教会史》第三部 福音三临453628390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应焕强 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 评介Documento6 páginas应焕强 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 评介YING Huanqiang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的实质Documento17 páginas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的实质Peter Jianmin Zhao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藏傳釋迦牟尼佛傳-一個宗教史學的分析Documento15 páginas藏傳釋迦牟尼佛傳-一個宗教史學的分析Low Beng Kiat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众神喧哗之地:西差会入闽(二)李伟斌Documento13 páginas众神喧哗之地:西差会入闽(二)李伟斌l1607986787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天主教在澳門Documento63 páginas天主教在澳門Dio Chan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建立在批判社会现实上的道德 - 卡莱尔英雄史观论 (下) - 林芊Documento7 páginas建立在批判社会现实上的道德 - 卡莱尔英雄史观论 (下) - 林芊song li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中国教会史Documento101 páginas中国教会史Long Jiao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 一本嘗試之作》導論Documento7 páginas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 一本嘗試之作》導論Josiane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人文主义精神 杨林Documento3 páginas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人文主义精神 杨林zhi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正教与异端Documento100 páginas正教与异端hankc james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解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 使徒保罗到改革家马丁·路德 姜守明Documento8 páginas解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 使徒保罗到改革家马丁·路德 姜守明dididi blue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35荷蘭統治之下的Documento33 páginas35荷蘭統治之下的CC Chen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中国内地会简史》Documento26 páginas《中国内地会简史》guangyu Lu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互爱不仅是友谊:马丁·路德论宗教与人生 (肖安平)Documento162 páginas互爱不仅是友谊:马丁·路德论宗教与人生 (肖安平)Nicholas Ng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駁于連Documento20 páginas駁于連Wen Yang Song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论科学与宗教之关系 (比)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著 余三乐 译Documento10 páginas论科学与宗教之关系 (比)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著 余三乐 译622 yn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Documento96 páginas《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Pietro Shao100% (2)
- 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 PDFDocumento15 páginas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 PDFDocumento15 páginas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康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 - 波爱修斯之死事件探析Documento15 páginas康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 - 波爱修斯之死事件探析liuy921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基督教問答大綱Documento15 páginas基督教問答大綱Cecilia Chan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蒋友仁与中西文化交流Documento12 páginas蒋友仁与中西文化交流Kwanyiu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浅谈中国教会的福音本土化Documento22 páginas浅谈中国教会的福音本土化Pietro Shao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天主教教史在华Documento20 páginas天主教教史在华MARIA 2016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Reform Study GuideDocumento16 páginasReform Study Guidejeepjeep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梵二会议与宗教对话 兼论神学建设的学术视野 张志刚Documento7 páginas梵二会议与宗教对话 兼论神学建设的学术视野 张志刚punpun0586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C3A3 UHIS 20200415 中国史考纲3.6要点Documento4 páginasC3A3 UHIS 20200415 中国史考纲3.6要点pooh100% (1)
- 宣教歷史 李品璇 論文Documento35 páginas宣教歷史 李品璇 論文Cathy Lee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第七期通訊Documento31 páginas第七期通訊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100% (1)
- 21-27 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閱讀報告.李品璇Documento1 página21-27 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閱讀報告.李品璇Wingate Manor College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当代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 以卡尔 拉纳与约翰 保罗二世为例 王新生Documento19 páginas当代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 以卡尔 拉纳与约翰 保罗二世为例 王新生cordeliawan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沉冤千年還可以翻身嗎? - 聶斯托利派被定為異端的思考Documento6 páginas沉冤千年還可以翻身嗎? - 聶斯托利派被定為異端的思考ji jack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沉冤千年還可以翻身嗎? - 聶斯托利派被定為異端的思考Documento6 páginas沉冤千年還可以翻身嗎? - 聶斯托利派被定為異端的思考ji jack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中国 封建 概念的演变和 封建地主制 理论的形成Documento28 páginas中国 封建 概念的演变和 封建地主制 理论的形成api-3699895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耶穌會士韓國英與《孝經》Documento29 páginas耶穌會士韓國英與《孝經》hpoplar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評論:林子淳。《存在‧歷史‧神聖: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Documento5 páginas評論:林子淳。《存在‧歷史‧神聖: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李元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中国礼仪之争 儒、耶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PDFDocumento8 páginas中国礼仪之争 儒、耶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中西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之争" PDFDocumento4 páginas中西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之争"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中国礼仪之争 儒、耶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PDFDocumento2 páginas中国礼仪之争 儒、耶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PDFThuận Trương Anh0% (1)
- 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 PDFDocumento15 páginas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PDFDocumento12 páginas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中国"礼仪之争"的再思考 PDFDocumento3 páginas中国"礼仪之争"的再思考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中西文化的一次剧烈冲突 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之争" PDFDocumento5 páginas中西文化的一次剧烈冲突 论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之争"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中西"礼仪之争"与中国近代化转型 从话语之争到身份之辩 PDFDocumento6 páginas中西"礼仪之争"与中国近代化转型 从话语之争到身份之辩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基督教第三次入华与康熙末年的禁教,历史教学, History Teaching,2005年06期 PDFDocumento6 páginas基督教第三次入华与康熙末年的禁教,历史教学, History Teaching,2005年06期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PDFDocumento4 páginas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从百年"礼仪之争"看中西文化的冲突 PDFDocumento3 páginas从百年"礼仪之争"看中西文化的冲突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礼仪之争"研究综述 PDFDocumento4 páginas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礼仪之争"研究综述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 PDFDocumento15 páginas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 PDFThuận Trương Anh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2高口1第3课 1(有讲解)Documento23 páginas2高口1第3课 1(有讲解)Weronika Gorycka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宋代科举与理学Documento8 páginas宋代科举与理学api-3699895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投資台灣 (修正本)Documento16 páginas投資台灣 (修正本)楊晟輔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Brochure Generali LionTycoon Beyond 忠意跨越創富保小冊子 (EN)Documento21 páginasBrochure Generali LionTycoon Beyond 忠意跨越創富保小冊子 (EN)AAKASH GOPAL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历史笔记Documento40 páginas历史笔记J323 35 TEE WAN LIN郑婉棱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
- 2.1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Documento179 páginas2.1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sabila fauzannissaAún no hay calificaciones